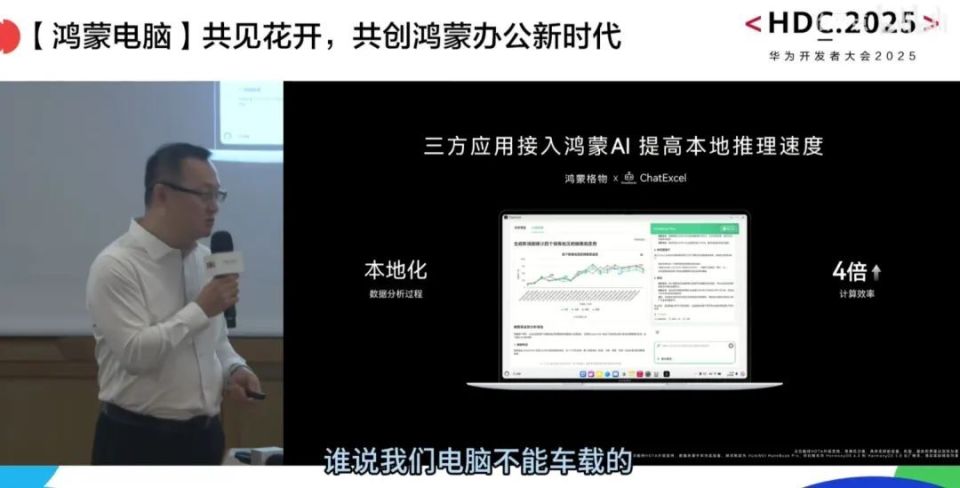在“建立校园防性侵保护体系”圆桌对话环节,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周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卜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教育官员苏文颖等嘉宾针对加强学校管理责任、提升儿童自我保护意识,以及通过法律监督推动“双向保护”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完善儿童权利保护框架
学校是未成年人生活学习时间最长的地方,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表示,让孩子在健康安全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学校责任义不容辞。作为人大代表,她曾建议由专岗来做未成年人防性侵工作,明确专岗责任的同时,也需加强每一位老师和教职员工的责任义务意识,在学校日常管理中,定期对校园环境、师生关系有常态化监督,及时排查可能发生的性侵风险点。而一旦发生校园性侵案件,学校应及时报告,不能瞒报、迟报。
在完善法律法规和学校用工制度方面,方燕提出,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入职查询制度要落到实处,如学校招聘教职工时,除常规的学历、工作经历审查外,要重点查询应聘人员是否有性侵、猥亵等违法犯罪记录或与此有关的投诉举报记录,还应建立定期审查机制,对在职教职工定期进行背景复查,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解除聘用合同并依法处理。
同时,方燕建议由公安部门牵头,联合法院、检察院、教育主管部门等,共同建立“全国性侵犯罪黑名单平台”,让广大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用人单位有效使用,希望能够有性侵犯罪记录的人员远离孩子,远离校园。

·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 方燕
就目前乡村校园防性侵工作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卜卫介绍了一些研究发现,基于近年来对乡村校长和教师培训经验,她认为还有三个方面有待提升:一是提高对反暴力的认识,比如如何理解基于性别的暴力,不仅因为是女孩,也可能因为性别刻板印象而受到暴力或骚扰,再比如如何理解孩子之间的“玩闹”或“叫绰号”是否是暴力,“当然以受害者的感受为金标准而不是以施暴者的辩解为标准。”
二是普及有关学校保护的信息和知识,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十八条,都提出学校要建立防止欺凌、性侵和性骚扰的专项工作制度,在与乡村校长制定机制模板的过程中,每一部分都需要专门的信息和知识。
三是明确儿童权利的价值观。卜卫强调,“儿童参与本来就是儿童基本权利之一。反对针对儿童暴力的全球运动有一个范式转型,即不仅仅将儿童看作是受害者,他们可以也应当是积极的行动者。儿童参与才能真正阻断暴力的代际传递。”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卜卫
“严惩犯罪的同时,预防是最好的保护”
“女童保护”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的205起性侵儿童案例中,可统计出施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有18起,在案例中占8.78%,施害人的年龄最小的仅13岁。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容易受环境和朋辈影响,未成年人被侵害后,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助,无法摆脱困境,就有可能被侵害群体“同化”,出现“恶逆变”。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周海波表示,检察机关坚持“惩治犯罪”与“保护救助”并重,积极推动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机制的构建。
首先是严厉打击组织和利用未成年人犯罪。周海波介绍,2024年,检察机关起诉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2000余件、5000余人,同比增长接近一倍;起诉强迫、组织、容留未成年人卖淫罪2000余件、4000余人,同比上升约14%。通过办案,及时惩处以未成年人为目标的性侵犯罪,有效维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
其次是开展综合救助保护。周海波表示,最高法、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要求发现性侵害案件后第一时间评估被害人状况,及时开展救助。检察机关与教育部门联合开展“控辍保学协作机制”,对案件中发现的辍学未成年人及时通报教育系统,协助复学,防止失学失管引发进一步违法行为。同时,对因家庭监管不力导致夜不归宿、沉迷网络等问题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将制发“督促监护令”,并联合妇联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周海波
再次是积极开展一般性的犯罪预防。“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平安校园建设,以法治副校长为抓手参与学校安全治理,促推学校健全防校园欺凌长效机制。”周海波说,检察机关还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推动宾馆业落实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减少未成年人受害风险。
“我们一直相信‘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希望能与社会各界一起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周海波说。
“防性侵应融入课程体系,老师也要接受培训”
在通过教育来提高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权利意识这一问题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教育官员苏文颖提出,教育是预防里最关键的一环,尤其需要在教育体系内和学校日常教育过程中涵盖相应内容。
苏文颖表示,一方面,有效的教育不是一次性的“疫苗”,而是需要像种树一样长期灌溉培育,比如将其融入到学校课程,特别是身心健康、社会情感学习等教育内容当中,目前其他国家已有一些将性健康教育或防性侵相关内容融合到日常教学的长效机制值得借鉴。另一方面,教师和教职员工也需要接受相应的培训,“中国防治未成人性侵的法律政策顶层设计已初具框架,为校园防性侵、防欺凌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在实际执行中仍存在落地细节不足的问题。比如很多老师对‘强制报告’并不了解,或者只听过这个名词,具体什么情况下触发强制报告,发现学生有哪些异常征兆可能表明有遭受性侵的风险?这些知识也需要培训来普及”。
苏文颖介绍,一些国家对学校教师和教职员工有明确的行为准则,且非常详细和落地,比如哪些是安全范围内的身体触碰,哪些是不允许的;师生单独相处的界限;学校的卫生间、更衣室、宿舍设施和管理有哪些注意事项;教师、教职员工和学生在社交平台上的交流边界等等,“这也是我们今后工作中可以去借鉴的”。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教育官员苏文颖
此外,她强调孩子本身有主体性,他们不应该只被视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孩子可以认识和行使自己的权利,用自身或同伴的力量发声,促进更多的意识提高和行为改变。因此,需要构建儿童友好的求助渠道,让孩子敢说、愿说、安全说。同时推动积极的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园内持续宣传尊重、平等、非暴力的价值观,让学生成为校园安全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
而提到近年来出现的网络性侵案件,如对“隔空猥亵”、游戏内诱导暴露隐私的预防,卜卫认为提升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或网络素养教育固然重要,但更还必须有社会性别教育,比如,可以教给孩子辨别真假以及抵制各种商业诱惑,但如何对待传统性别规范的各种“规训”、“性”羞耻(或“荡妇羞辱”,经常被坏人用来威胁)等,需要性别平等方面的教育。